云看展 | 一幅画的诞生:乐祥海《桃园日记》2020-05-12

乐祥海简历

乐祥海,笔名大乐。1971年9月出生于河南省息县。博士。1990年开始漫画创作,1999年起师从李世南先生,专攻写意人物画。现为北京画院专业画家、艺术委员会委员、研究员、艺术部主任、传统中国绘画研究中心秘书长,为国家一级美术师、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北京美术家协会理事、全国青联委员。
我怎么创作《桃园日记》





乐祥海 桃园日记 2019年
28cm×36cm×5 纸本设色

《桃园日记》局部
如何在作品里体现自己当下的真实感受,是当代画家必须面对的课题。《桃园日记》是我在北京东四环路边一片桃花园里的现场写生。画桃花已经四五年了,这是我首次现场对景创作,之前给自己提出了要求,不可以去简单地描摹对象,而是要画出自己看到对象后的一种感觉。
当初画桃花的动机,是因为那些经过嫁接或专门培育出来的桃花,看起来是那么不真实,似乎隐藏着这个世界的秘密,表面繁华却浮华,表面红艳却凄艳,表面装饰却粉饰,有的根部和树干的部分,已经走入枯萎态,但在表面上,它们在支撑着一种虚假的、貌似的繁华景象。……这不是人吗 ? 这不是我吗 ? 活在当下,每个人都是不同程度的受伤者,为了在这个社会中生存下去,很多人在打肿脸充胖子,大多时候被迫把最虚浮的一面呈现给世人。
我并没有太多观照传统意义上的“花鸟”画,虽然是在记录桃花旺盛的生命力和四溢的激情,却尽最大的努力尝试完成桃花在尘世的影射和隐喻。它们张扬着一种现代感的媚态,这种媚态带着一种孤绝性和狂野性,跟当下都市的生活状态有某种契合点。于是,有时候我特意让它们呈现出受伤后的肿胀,痛感与美艳并存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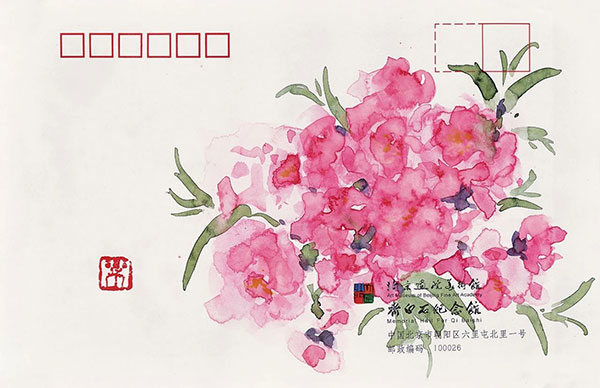

《桃园日记》画稿
由《桃园日记》延伸出的话题
从河南到北京


我十六七岁时,高一辍学,到东北务工,曾在北京转车,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农村出远门,记忆当中北京的火车站非常气派,当时并没有把自己与这个城市做过任何联系。
2001 年夏,我首次“正式”来北京,当时是以《东方艺术》杂志编辑的身份到宋庄画家村做了两天采访,走门串户,清一色的秃瓢、光背、大裤衩子加拖鞋,那些“流浪”画家几乎个个都是一副典型的农民模样,他们的生活状态颇让我羡慕。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日子过得非常拮据,甚至家徒四壁,吃了上顿没下顿,但我依然觉得他们是非常幸福的,可以随心所欲,自在、逍遥地在那里画画和生活。而我,自离开校园后几乎放下了画笔,终日为生计奔忙,虽然很顺利地挣了点小钱,但内心深处并不快乐。
第二年,作为主编的我,为了发行,又来到北京,沿街给报摊送杂志。记得当时驾着车行驶在长安街上,一股扑面而来博然之气,眼前的路如此宽阔,这个城市瞬间给我一股莫名的吸引力。那时,我正跟随李世南先生习画,适逢他要结束在郑州的暂住而定居北京,我遂决定处理掉在河南正经营不错的企业来京发展,当时竟没有丝毫犹豫。
那当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步。
现在成为北京画院画家中的一员,非常感恩。
直指本心


在学习的道路上,李世南先生引我入门,艺术观之形成完全受他影响,先生教我明白:绘画状态就是生命状态,此乃颠扑不破之真理。
中国传统中,我喜欢的画家有倪云林、徐渭、陈洪绶、八大山人、黄宾虹、关良等,西方则心仪高更、凡 · 高等。
我下了很多功夫学习、研究黄宾虹和关良。黄宾虹属于“国粹派”,他在从事古玺印金石文字的搜集、整理、研究,美术史的治学,古书画的鉴定,积稿逾万的古画勾摹,艺术创作的“笔墨论”等方面,完全是这一文化立场的展现。黄宾虹秉持“民学国画”观,强调创作应以人为本,是艺术家的一种自我精神的表达,尽情表露其审美旨趣及修养境界,所谓游于艺。与之相对应的“君学国画”,创作是为他人的需要,枉己徇人之意存于其间,这就局限了艺术家个人对审美理想的追求和表达。艺术价值高低的最根本原因,就在这“为人”与“为己”的创作动机不同上。黄宾虹在笔墨的探索及运用上成就是巨大的,视笔墨为中国画的生命,并总结出了“七墨法”,提出国画当“墨妙笔精”,认为“笔力为气,墨彩为韵,千变万化,入于规矩之中,而超出规矩之外”。黄宾虹将笔墨的审美价值升华至出神入化的境界。他赋予笔墨新的内涵,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“毛笔”和“墨水”,也不是外在的线条和墨的形式,它不但是画家作为状物、传情、达意的表现手段,又是表现对象的载体,更是画家修养的体现形式,它与画家的思想境界是一脉相通的,它甚至可以跳出物象形态之外而独具魅力,也可以说它是画家个性品格、知识修养的直接载体,是作品的“内容”。文人画的发展无疑带动了笔墨的发展,笔墨具有了干、湿、浓、淡等丰富的情态,随之又出现了各种皴法及墨法,这使得画家更能够充分、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情感,凸显了笔墨的独立审美价值。笔墨的上述内涵在山水、花鸟画当中得以完全呈现。然人物画是以人物形象为主体的绘画,要画好人物画,就必须有塑造人物“形象”的能力,即所谓“造型”。在传统中,要求人物画家必须了解和研究人体的基本形体、比例甚至解剖结构以及人体运动的变化规律,这样方能准确地塑造和表现人物的“形”和“神”,而人物画传统的基本画法 —— 白描法、勾填法也是为此服务的,画家的一笔一线都是不能偏离所描绘人物的。相对而言,山水、花鸟画在此方面,“形”的限制显然自由度要大得多,或者说有很大的“发挥”空间,笔墨也更容易表现为“自由”“解放”的状态。关良却把此引入到人物画的创作中,不拘泥于对象的解剖、透视和比例,线走中锋,质朴稚拙。比起传统的用笔方法,关良的用笔方法更加直率、简捷、执着,更加“直指本心”。笔线极具力量,墨色富于变化,突出了笔墨的自由与情趣,与黄宾虹“内美”思想及用笔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。用笔在中国画里面是有特殊意义的,它几乎可以成为是不是“中国画”的唯一标准。关良先生在用笔上做出的成就,对有志于继续画中国画的我们这些后辈来说是绝对不可忽视的。
笔迹乃心迹


艺术创作的意义或者说其成立的前提,当然在于作品的创造性。不同于古人,不同于今人,要有独立的面貌。同时,还要求这种“创造”是自然的、本真的。拿绘画来说,应该是画家生命状态的真实反映,画家性格开朗,画必畅达;画家清高文雅,画必绝俗;画家人生凄凉,画必苦涩;画家性格膨胀,画必虚狂……对于画家来说,笔迹乃心迹。如果画家很有内涵,不必刻意追求,画自然也不会浅薄;同样道理,如果画家很世俗,任凭怎么包装,断是高雅不了的。这是艺术创作的大规律。
当然,在没有信仰的社会,环境决定画家的生命状态,也就是说,画家的艺术创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影响。逢繁荣盛世、国泰民安,艺术创作自然也会呈现一片阳光向上的面貌;当国破家亡或社会矛盾激化时,画家的作品显露的必是凄苦与挣扎。不可否认历史上有很多画家看破红尘,或隐于山林,或遁入空门而远离世俗,他们的作品非常“出世”,对于这种情况,我们不能简单视之为不受社会环境影响,相反,这恰恰是社会现实作用于画家的结果,只要去对这些画家的人生状态深而究之,会发现社会现实对这些画家的影响更甚。
放眼传统,历代中国画大家都具有极高文化修养及思想境界,因为以前有大的文化氛围与土壤,画家的基础、起点非常高。传统的逐渐势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当下中国画的创作,起点越来越低,很多画家缺少了起码的人文底蕴,失去了文化的滋养后,和前人差得越来越远,作品流于表面,只剩下技法与形式,没有了任何思想高度和品味空间;也有一些“精明”的画家妄图抄“近路”,“设计”了一套风格面貌,成名成家,反而过早结壳把自己束缚住了;与之对应的,还有一批自言要“坚守”的“伪传统”者充斥于当代画坛,他们抄袭前人的“形式”,并谓之为中国画正统。活在当下,心境与状态自然不可能与古人相同,如果仅仅去对传统“相貌”简单描摹,只能算是传统的“行尸走肉”。
乐在其中、乐此不疲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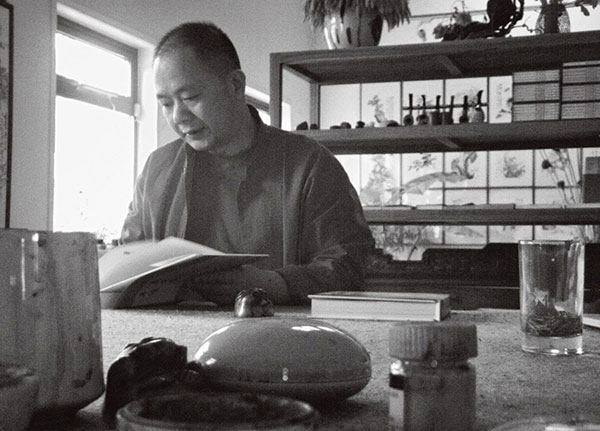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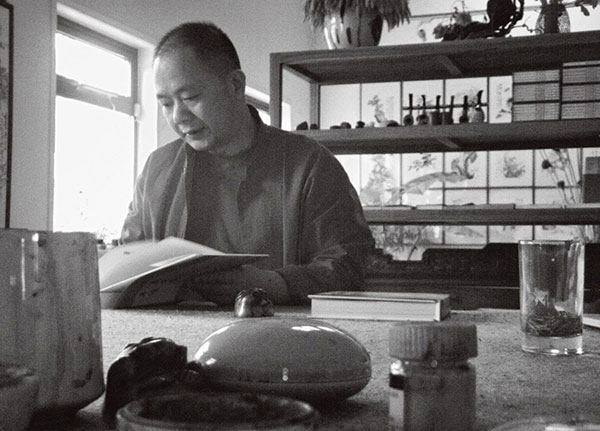
我想通过对前人的学习与借鉴,真诚地表达自己对世界和生命的认识,对造物主的颂赞。我本是一个俗人,人间烟火不时影响着我的情绪,喜怒哀乐,我的画就是我某一段情绪与感受的真实记录。
有人说你画这样的人物一点也不美,毫无卖相。其实我不是不想往“美”了画,也不是不想卖画。说来也怪了,尝试若干回,竟画不出一张“美”人儿来,一出手便是“歪瓜裂枣”,凄凄惨惨,一脸苦相,哪怕我拿俊男美女摆在眼前当“本子”,终也无济于事。满纸的失落、迷茫、彷徨、无助、忧伤、悲壮、挫败、无奈、虚妄、弱智、狡诈、欺骗、自负……为什么会这样?至今自己也很难说出个所以然来。可能还是因为我的层次太低,加上社会的另一面给我的影响太深,属于“见山是山”的水平。时间长了,自己在生活中也常常会表现出笔下人物的“表情”来,悲摧得很,老是莫名生出恼火。后来我竟有所悟,一声长叹,可能这就是传说中的“天注定”,自己原本就这“使命”,那画中之人就是另一个我。想通了就顺畅了,希望自己一直保持“业余”的心态,在此状态下,自己的压力不大,兴之所至,不必过多地考虑美术展览的“评选标准”与市场上收藏家的口味,乐在其中,乐此不疲。
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1011
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1011